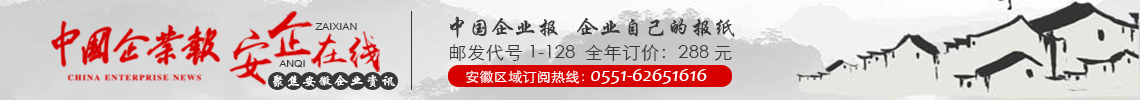郑万全(55):以敬畏之心行慈悯之道
时间:2025-09-05 17:20来源:中国企业报看安徽 作者:明骅英
作者:明骅英 五十余载的行医路,郑万全的白大褂上早已浸满岁月的痕迹,却始终保持着对生命最纯粹的敬畏。这位年近70岁的基层医生,用百万张处方丈量着从医的长度,用二十余载诗歌创作拓宽着人文的宽度,更以以敬畏之心,行慈悯之道的信念,在医学与文学的交界地带,筑起一座连接生命与自然的精神桥梁。 2025年6月12日清晨,天光微亮时,郑万全伏案写下《明者之心》
作者:明骅英

五十余载的行医路,郑万全的白大褂上早已浸满岁月的痕迹,却始终保持着对生命最纯粹的敬畏。这位年近70岁的基层医生,用百万张处方丈量着从医的长度,用二十余载诗歌创作拓宽着人文的宽度,更以“以敬畏之心,行慈悯之道”的信念,在医学与文学的交界地带,筑起一座连接生命与自然的精神桥梁。
2025年6月12日清晨,天光微亮时,郑万全伏案写下《明者之心》:“你我为天下,日夜在飘香。山水添神仙,天地送风光。”短短二十字,如同一剂浓缩的良方,既藏着他五十年来的行医之心,也裹着对世间万物的深情。作为诊疗人次吉尼斯纪录的申报者,他见过太多生老病死,却从未让麻木侵蚀内心的柔软;作为出版多部诗集的创作者,他笔下的草木山水皆有灵性,只因他坚信“人的灵魂来源于自然”。

“你我为天下”的格局,是郑万全从医第一天就刻进骨子里的誓言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年轻的郑万全就背着药箱穿梭在乡村小路,泥泞沾满裤脚,蚊虫叮咬肌肤,却挡不住他奔赴患者家中的脚步。
那时的乡村医疗条件简陋,听诊器和体温表是最“先进”的设备,他却凭着一股“健康天下、医治人间”的执拗,将诊所开成了村民心中的“生命驿站”。五十多年来,他累计开出百万张处方,其中2.8万张是分文未取的免费单据——遇上来不及带钱的急症患者,他先治病再说;碰到家境贫寒的老人儿童,他默默划掉药费。
有人劝他“医者也要谋生”,他却指着墙上“但愿世间人无病,何惜架上药生尘”的题字笑答:“比起赚钱,看着患者康复的笑脸更让人踏实。”生活中的他,常以“一碗稀饭就咸菜”果腹,却把省下来的钱换成药品送给需要的人。这些看似平凡的选择,恰是“日夜在飘香”的生动注脚——如同山野间默默绽放的花草,不求人知,只为给世界添一缕芬芳。

在郑万全的世界里,医学与文学从来不是割裂的存在。他的诗中,“山水添神仙”的意境绝非凭空想象,而是源于常年在乡村行医时对自然的细致观察。一次冒雨出诊,他在山路上看到被暴雨打蔫的野花,次日路过时却发现它们重新挺直了腰杆,遂写下“雨打花枝暂低头,风停再向太阳稠”的诗句,既记录了自然现象,也暗合了他对生命韧性的感悟。
这种“草木有灵”的生态哲思,在他的《望天门山》等诗作中亦有体现,他曾在诗中写道:“一石一木皆含理,一花一叶总关情”,将医学中对生命体征的关注,延伸为对自然万物的共情。他将这种创作理念称为“生命诗学”——“医生看病是关注人的生理生命,诗人写作是探寻人的精神生命,而这两种生命,根源都在自然里。”这种跨界融合的探索,让他的诗集《悟诗》在出版多年后仍被读者珍藏。有读者评价:“读他的诗,能看到白大褂下的仁心,也能感受到山野间的灵气。”
对郑万全而言,诗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,更是为乡村医疗发声的工具。作为诊疗人次吉尼斯纪录的申报者,他并非追求“纪录保持者”的头衔,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更多人看到基层医疗的现状。
“很多人觉得城里的大医院才是医疗的全部,却不知道乡村诊所里藏着多少坚守。”他的诗中,“天地送风光”的豁达背后,藏着对城乡医疗资源不均的深沉思考。在《乡村医声》一诗中,他写道:“听诊器在乡野跳动,与城市的CT机同样沉重”,用朴素的语言揭示了基层医者的责任与压力。这些诗歌如同一个个文化注脚,让更多人透过文字,看到简陋诊室里彻夜不熄的灯光,看到背着药箱翻山越岭的身影,看到那些在医疗资源匮乏的环境中,依然努力守护生命的基层医者。
如今的郑万全,依然每天清晨五点起床,先在诊所后的小院里侍弄花草,再提笔写几句诗,然后穿上白大褂开始一天的诊疗。他的头发已有些斑白,双手因常年握听诊器、写处方而布满薄茧,眼神却依旧清亮。当被问及“行医五十年最骄傲的事”,他没有提那些荣誉与纪录,而是翻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,里面贴着患者送的感谢信,和他随手写下的诗句。
“你看,这些才是最珍贵的。”他指着其中一句“行医半世纪,未改是仁心”说,“只要还能拿起听诊器,还能写出诗句,我就会一直守在这里,继续走这条‘敬畏生命、慈悯世人’的路。”
郑万全的故事,恰如他笔下的山水风光——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,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。当我们品读《明者之心》的字句时,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医者的情怀,一位诗人的感悟,更是中国乡村医疗发展历程中,一个用初心坚守使命、用热爱点亮希望的生动缩影。
那些百万张泛黄的处方,那些浸润着草木清香的诗句,共同勾勒出一个大写的“人”字——既有对生命的敬畏,也有对世间的慈悯。
相关文章
- 10-01预售9.58-13.18万元 思皓曜年轻人的第一辆智能轿
- 07-27淮北矿业铁运处K车检修场上的车辆“美容师”
- 10-05【中铁四局员工国庆献礼】中铁爱国情
- 08-04雷鸣科化公司电子数码雷管在井下爆破成功
- 01-08首次OTA升级,捷途山海T1新增CarPlay+HiCar功能
- 08-22安徽省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推进座谈会在北京举
- 10-15涡北选煤厂创新机制强化安全管理
- 03-06孙疃矿双轮驱动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
- 01-21怀宁县启用安庆市首家县级7*24小时自助车管所
- 04-12再部署再强调 恒源矿做好疫情防控工作